作者:孙亦真
摄影:杨浦东
在许多人眼中,数学是高耸于抽象之巅的冰冷城堡,充斥着复杂的符号与公式。然而,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席南华看来,数学却是一片充满惊奇与美感的沃土,等待人们以纯粹之心去探索和耕种。近日,我们有幸走进这位数学家的思想花园,聆听他关于中国数学应如何“建设自己的花园”、研究者为何要“单纯地享受学问”,以及如何在理性逻辑中捕捉“无法形容的美”的深刻洞见。

席南华:给数学一个严格的定义是困难的。它研究“量”与“型”,但其他一些科学也研究。数学的典型特点是抽象,这是其他学科没有的。比如它研究的最基本对象——“数”,就是现实中的抽象,你在现实中找不到一个纯粹的“3”。它研究的数学规律也很难一言以蔽之,比如不同事物间的联系、存在性、分类等。
我们研究的“型”也是抽象的。几何中的点没有大小,线没有宽度。但后来我们发现,几何其实是一种结构,无处不在。起初你觉得数学简单,但越深入越发现其内涵的复杂与丰富。数学,归根结底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如同物理一样,只是它格外抽象和理性。这种严格的抽象定义有时与直观相差甚远,比如19世纪建立的严格的数论,普通人看了会觉得是“怪物”,但正是这些“怪物”般的严格定义,为现代科技奠定了基石。
席南华:这有几个原因。很多时候学习过程是不自由的,导向是做题目、完成学业,而非理解和欣赏数学。如果带着更轻松的心态,有更好的老师或书籍引导,数学的美就会显现。
数学的美有多重内涵。有形美,比如一些让人有惊艳之感的几何图形、一些简单函数迭代产生的图形、分形。但更多的是抽象思维的美。比如,三角形三条中线交于一点,这种出人意料的“巧合”让人惊奇。证明的简洁利落也展现了一种逻辑的力量,比如证明素数有无穷多个,或者证明根号二是无理数,过程清晰、有力,非常美。
此外,数学对象内涵的丰富性也让人惊讶。比如关于素数分布的问题,催生了素数定理、黎曼猜想,黎曼为此引入的黎曼ζ函数,其本身又被认为是“美极了”的,并引出了各种各样的L函数,以及研究不同方式定义的L函数之间联系的朗兰兹纲领等更深刻的数学。这种思维的深度和联系,是一种极致的美。
现实中复杂的问题,用数学语言可以优雅解决,如欧拉解决哥尼斯堡七桥问题,或证明任意六人中必有三个人互相认识或互不认识,都展现了智慧的魅力和思维的美。感受到这些,需要稍稍放下功利的心态,去体会其中的形美、思维美和内涵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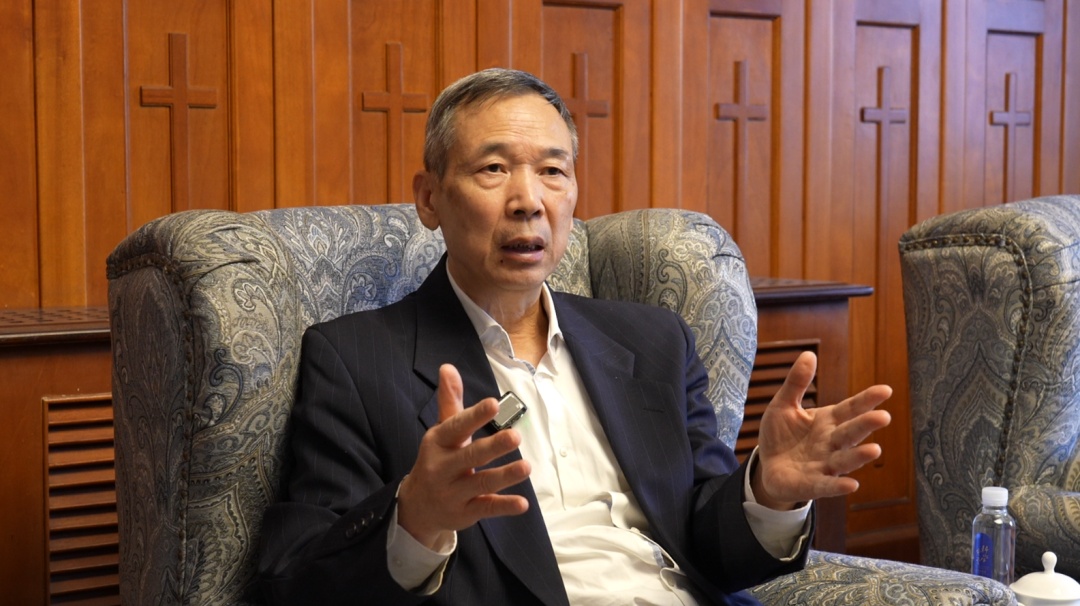
席南华: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数学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总体而言,我们仍处于跟随者的地位,可能是最好的跟随者。我们能在他人开创的领域里做出非常好的工作,引起同行关注。
但一个本质的差别在于:我们目前主要是在别人的花园里面种花种草,种得很漂亮,但我们自己开辟的、属于自己的“花园”还很少。如何建设自己的花园?这确实不简单。西方科技经过几千年发展,有其深厚的文化和社会思维根基。我们若只注重科技一面,会有不足。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同时,目前的评价体系有时不太利于做真正原创性的工作。科技界自身也需要反思,要有更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总依赖外力或政府。我们需要意识到,做科研是我们自己的事业。
席南华:这里就涉及一个核心问题:我们为什么做科学?我发现,西方很多科学家对科学充满感情,仿佛生命融入其中。相比之下,我们国家这种深深的情感投入还不多见。
做研究,需要一种单纯的心态。如果你非常单纯地只是想揭示世界的奥秘,那么其他东西都无关紧要。你会非常享受做数学的乐趣,发现数学的美。夏道行院士就是很好的例子,他95岁头脑依然清晰,对往事记忆犹新,这就是源于对科学的单纯热爱。
另外,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与西方差距巨大,向他们学习并得到帮助是必要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地忽略了自己的学术自尊和学术骨气。一个表现就是,现在很多媒体和学者仍把在“顶刊”上发表论文视为终极目标。这有很大问题。
第一,你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做出伟大的工作,而伟大的工作不一定非要在顶刊上发表。第二,对这种顶刊的崇拜,本质上是将评价权完全交给了别人,是学术独立性不足、自信不足的表现。如果你的工作是真正原创的,起初可能都找不到审稿人,因为没人懂。你能判断自己工作的价值吗?你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吗?目前的生态环境对此并不够鼓励。科技界首先要自己重视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能依赖外力。
席南华:我的建议是越单纯,走得越好、越远。把做学问看作一件快乐的事,没有必要让这份快乐被各种指标和别人的夸奖所引导。
你如果真正把研究做好了,做出了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帽子”之类的都是副产品,自然而然会来。如果你以“帽子”为导向,你的科研负重就太多了,这会消耗你的精力和内在心理资源,让你不可能走得很远。
现在青年学者的生存条件比我们的前辈好得多。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安心享受做学问的快乐,反而要引入那么多让自己不快乐的因素呢?就像匈牙利数学家雷尼(Alfréd Rényi)说的,“如果我感到忧伤,我会做数学变得快乐;如果我正快乐,我会做数学保持快乐。”他没有去想那些“帽子”。
当然,这背后有大环境的因素。但学术界和个人都需要想清楚:“帽子”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占多大地位?你是为“帽子”而生,还是为学术而生?这是有本质差别的。想清楚了,就知道该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