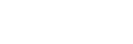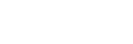国际著名物理学家
与大中学师生面对面
会碰撞出怎样的思维火花?
来看这场在海南举办的
华东师大“大师讲堂”
如何触发科学思考
传递科学精神——

“科学突破往往始于技术方法的创新。”“作为科研工作者,我的出发点始终是好奇心,渴望理解自然现象本身。”“科学探索的价值首先在于认识世界,然后才谈得上应用。”……在华东师范大学74周年校庆之际,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俄亥俄州立大学皮埃尔·阿戈斯蒂尼教授,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加拿大拉瓦尔大学陈瑞良教授应邀主讲华东师范大学“大师讲堂”暨校庆74周年系列讲座,并在华东师大海南研究院所在地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与大、中学师生对话交流。

皮埃尔·阿戈斯蒂尼、陈瑞良分别进行了学术报告,来自入驻高校、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等单位的500多位师生学者参加了此次讲座。
皮埃尔·阿戈斯蒂尼教授主讲华东师范大学“大师讲堂”暨校庆74周年系列讲座在以《Attosecond Flashes of Light: Generation, Applications and Beyond》为题的讲座中,皮埃尔·阿戈斯蒂尼以其荣获诺贝尔奖的里程碑式研究为核心,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阿秒量级(10-18秒)超快光脉冲的产生原理与技术突破。他形象地将阿秒脉冲比喻为“世界上最快的高速相机快门”,使得人类首次能够直接观测和操控原子内部电子运动的瞬时过程。陈瑞良教授应邀主讲华东师范大学“大师讲堂”暨校庆74周年系列讲座陈瑞良以《Lightning mechanismat the molecular level and forest wild fire》为题,以其在超快强激光科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为基础,深入探讨了雷电在分子尺度上的触发机理及其与森林野火形成的内在联系,重点强调了激光光丝远程稳定传输,成丝过程中诱导的气体膨胀,分子的解离,原子内部能级之间的粒子数反转,以及它的强度钳制效应,内部高密度等离子通道的产生等特性是支撑其众多应用的主要物理原因。您如何在这么长的学术生涯中始终保持科研动力与竞争力?当实验屡屡失败时,您如何调整心态、突破瓶颈?
皮埃尔·阿戈斯蒂尼:理论是行动的基石,任何实验都离不开坚实的理论指导、周密的计划与计算。困难是常态,我在实验过程中遇到无数次的失败,数据的波动和不确定性也是探索过程中的一部分。其次,坚持与反思是关键,我的学生在读博时也会非常担心能不能完成任务,受到了各种挑战,在几周的困境后,通过持续反思与尝试,最终能找到突破口。
报告中提到,阿秒脉冲可用于观测电离过程并消除成像虚影,是否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从观测电子动力学到主动操控化学键的断裂与形成,并将这一技术应用于原子级精度的表面修饰或更精密的光谱探测领域?
皮埃尔·阿戈斯蒂尼:这在分子尺度上是完全可行的。原子物理学中用于检测电子动力学的相位测量等技术,为我们在分子层面实现化学键的操控提供了理论基础。正如阿秒科学从理论走向应用,科学的魅力就在于保持探索的勇气,将想象变为现实。
我在学习物理时遇到两个困惑:第一,在构建物理模型时,如何判断哪些模型是客观存在的,哪些是虚构的?第二,当实验数据与理论假设不符时,我们应该如何调整假设或改进实验方案?
皮埃尔·阿戈斯蒂尼:模型的价值在于解释或者预测现象。当假设与实验不符时,这正是深化认识的契机。我们获得诺奖的关键就是突破了阿秒测量技术,首次观测到电子绕核运动的过程。科学突破往往始于技术方法的创新。

低纬度形成的雷雨云在从低纬度飘向高纬度过程中,路上那么远,它的电荷为什么不会在路上就释放掉呢?
陈瑞良:会被释放掉,只是不多。由于空气中带电粒子的阻力及正负电荷在云层中分布不均(正电荷多在上层、负电荷多在下层),使得云层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远距离迁移。强风、稳定的大气层结等特定条件,都能有效阻止电荷在途中过早释放。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是否已出现一些有望在更微观层面取得突破的苗头性研究?微观世界由量子力学主导,很多现象无法用经典理论解释。当前是否有这类前沿探索,可能推动向更微观尺度实现理论突破?
陈瑞良:我的第一个简单回答是:我不知道。如果要我进一步讨论,我想说探索未知无非两条路径:一是通过理论计算验证想法是否可行,二是通过实验去亲眼见证。科学研究越走向深处,实验技术要求就越精密,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做不到。正如今天有同学问到研究中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这让我想起自己攻读博士时的经历。当时我的导师让我搭建一套真空系统来探测多光子电离原子现象——这个领域我们都不熟悉。但正是通过亲手搭建每一个部件、克服每一个困难,我们最终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研究道路。
陈瑞良: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海南作为热带地区,植物叶片大、水分多,其实很难持续燃烧。雷电可能把树干劈成两半,但潮湿的环境让树木很难烧起来。不过要注意,所以下雨打雷时,可千万别站在树下——连我都不敢站在那边呢!
刚才您解释了雷雨云从低纬度向高纬度移动的规律,这项研究在实际应用层面能解决哪些具体问题?
陈瑞良:关于具体应用,我目前还无法给出明确答案。作为科研工作者,我的出发点始终是好奇心——渴望理解自然现象本身。科学探索的价值,首先在于认识世界,然后才谈得上应用。
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俄亥俄州立大学名誉教授
皮埃尔·阿戈斯蒂尼
(Pierre Agostini)
1941年7月23日出生于突尼斯,1968年获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博士学位,1969年—2003年,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巴黎萨克雷大学分会(CEA Saclay)研究员,1999年—2002年,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巴黎萨克雷大学分会(CEA Saclay)研究主任,2004年任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系教授,2018年任俄亥俄州立大学名誉教授。皮埃尔·阿戈斯蒂尼教授的工作领域是超快光子学。1979年,他第一次发现了激光与原子作用时的阈上电离,2001年实验实现250阿秒(10-18秒)超快激光输出,发明测量阿秒光脉冲的RABBITT(双光子干涉的阿秒拍频重构)技术。因为“采用实验方法产生阿秒脉冲光,用于研究物质中的电子动力学(for experimental methods that generate attosecond pulses of light for the study of electron dynamics in matter )”,202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国际著名物理学家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教授
陈瑞良
(Seeleang Chin)
1942年5月24日生于马来西亚,1969年获得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理学博士学位,随后长期在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工作,2001—2014年任加拿大超快强激光科学研究讲座教授,2014年起任加拿大拉瓦尔大学荣休教授,2008年获得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荣誉博士,2011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荣誉教授。
陈瑞良教授在强场激光物理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在该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发表论文490余篇,被引22000余次,曾荣获加拿大物理学家协会最高奖——终身成就奖(2011)、美国光学学会会士(1995)、德国洪堡研究奖(2001)等荣誉。他在实验上证实了原子分子的多光子电离效应,发现了多光子电离的饱和效应。1985年首次从实验上验证了隧穿电离理论,澄清了关于隧穿电离理论长期的质疑。隧穿电离最终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高次谐波和阿秒科学(诺奖得主Pierre Agostini在诺奖官网自传中强调了这一里程碑性成果)。此外,在非线性光学新的分支——飞秒强激光成丝科学领域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引领其在基础物理和应用研究等领域的发展。
当天,皮埃尔·阿戈斯蒂尼与陈瑞良一行参观了华东师范大学海南研究院海洋精密光学仪器研发中心,了解该中心在平台建设、技术攻关、理论创新和装备创新等多个层面取得的系列突破性进展。

海洋精密光学仪器研发中心当前聚焦超快激光调控技术,主要涵盖红外单光子操纵与控制、海洋分子指纹光谱、超快激光动力学、超快激光加工与检测四个关键领域。

海洋精密光学仪器研发中心负责人曾和平详细介绍了研发中心的发展现状和研究成果。中心师生及科研人员与两位教授就超快激光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包括新型激光器研发、多学科融合创新以及技术产业化路径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

本次活动由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海南研究院联合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市珠崖毓才院共同举办。
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大师讲堂”学术品牌活动首次在沪外举行,是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4周年系列高端学术讲座的亮点部分,也是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活动吸引超千人线下报名,近3000人线上观看直播。
来源 | 海南研究院
编辑 | 符哲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