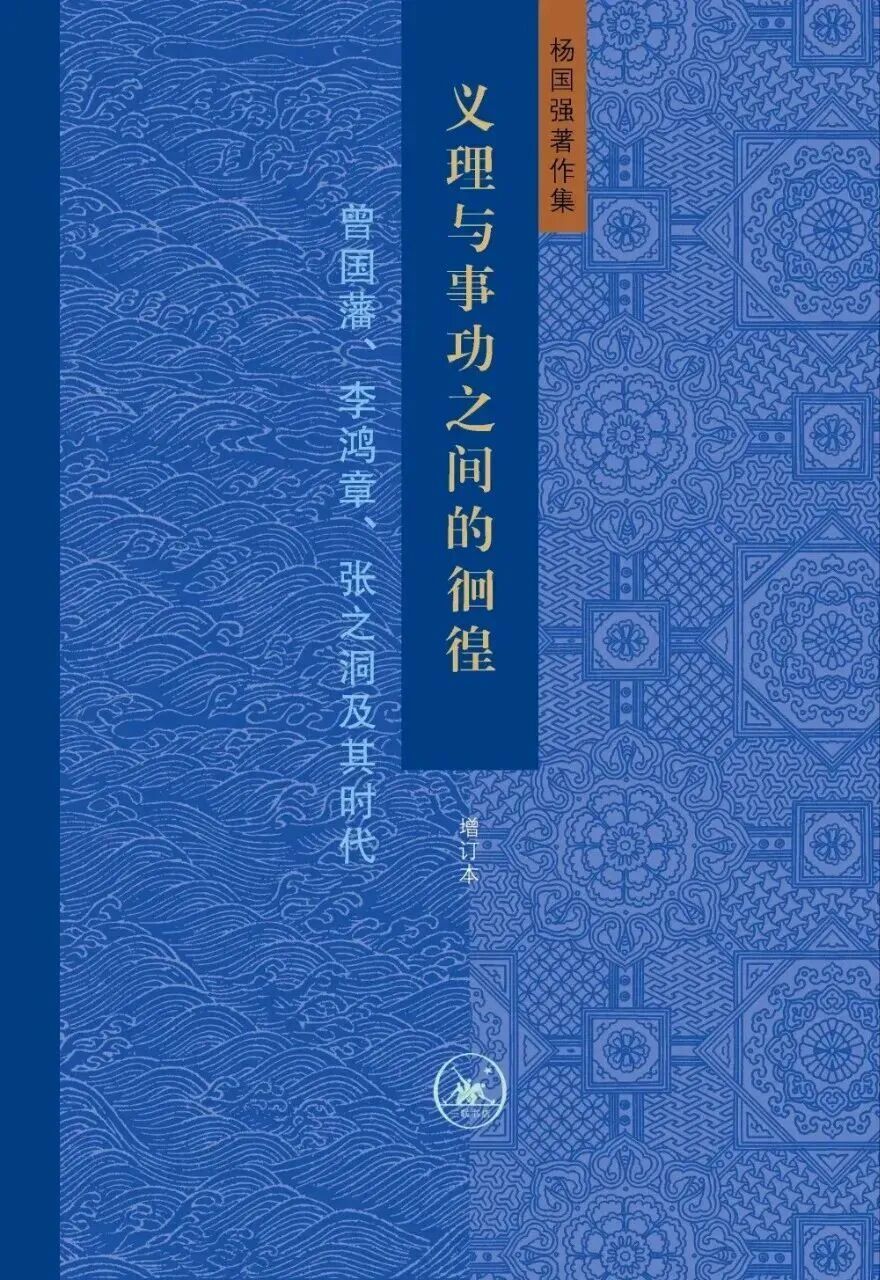
《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及其时代(增订本)》
杨国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7月

新版序:理势交困之下的人随时走和心长力绌
曾国藩论(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曾国藩论(二):从经世之学到西学东渐
李鸿章论:没有义理之学的洋务巨擘
读史断想:庚申与甲午之间的中国社会
世路跌宕中的“先人而新”和“后人而旧”
张之洞与晚清国运
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
后记
后 记
文 | 杨国强
二十多年之前随陈旭麓先生学史,最先用学问功夫读的便是《曾文正公全集》和《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之后,是以胡文忠公、左文襄公、李文忠公,以及沈文肃、彭刚直、丁文诚、曾忠襄、刘忠诚、张文襄、翁文恭,还有李越缦、王湘绮、盛愚斋、张季子等等为书名的各类辑集。正是沿着这些人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诗文,我才能够具体地进入19世纪中国的历史,进入19世纪中国士大夫的真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并由此形成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和判断。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而我记忆最深的则始终是读曾国藩。记忆深的东西总是心血化得多的东西,在陈先生门下的那三年里我写过四篇文章,其中两篇的题目都是曾国藩。今日重阅旧文,当年师门耳提面命之教犹历历如在眼前,思绪绵连,不觉怅惘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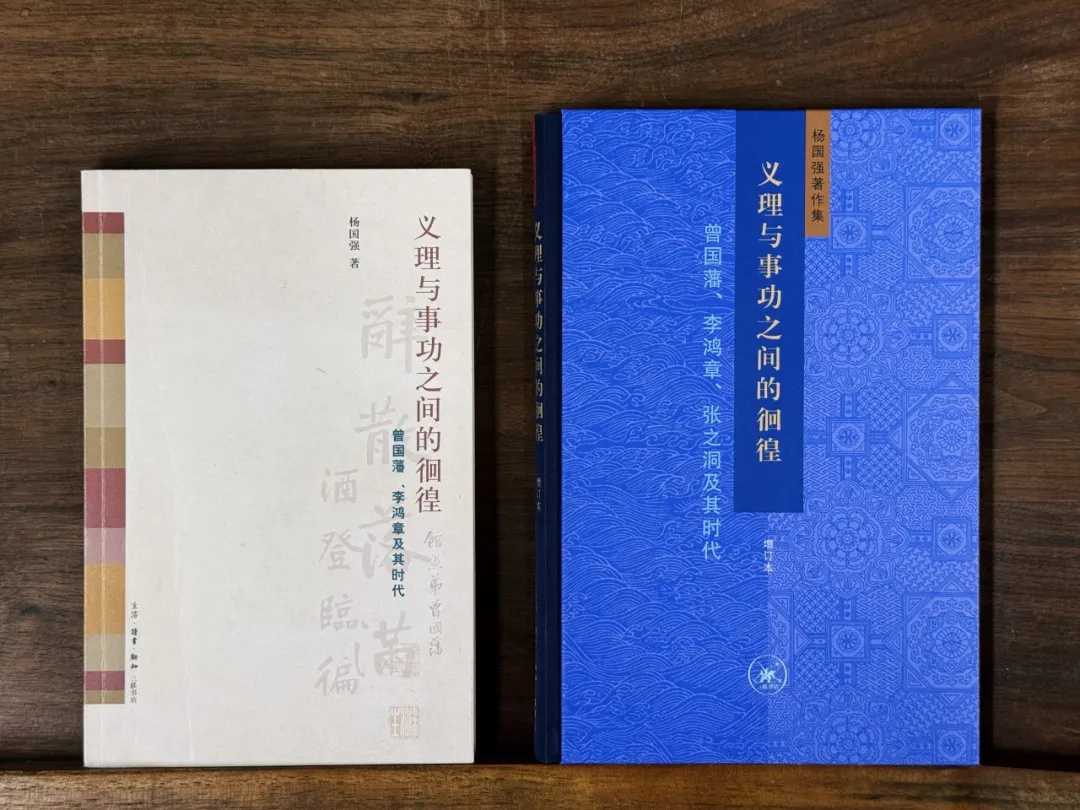
左图为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右图为本次推出的新版
当曾国藩被当作一个历史场景中的人物来追究和评说的时候,许多细节常常会过滤掉。然而,细节其实更读之有味而且言之有味。同治中期在两江总督幕府里的赵烈文称曾国藩为老师,其日记中记录过一段问答。他问的是:“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鸡鹜,亦食火腿否?”曾国藩回答说:“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彼时乡间的有田之家往往以坛藏绍酒为常事,然则“每斤零沽”便以其寒酸而能够成为一种感动。所以赵烈文叹为“大一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这一类日行起居虽然琐碎,而人格中的真实一面却常常因此而见。光绪间刘坤一作诗怀曾国藩,说是“事事不能及古人,立身窃与古人类;事事无殊于人,居心却与今人异。画鹄画虎在我写,呼牛呼马凭人戏。卓哉唯有湘乡翁,纷纷诸子谁能比”,着眼的也是这一面。当日曾国藩因事功而被称作名臣,但比事功更能耐久的其实还是人格。因此在后来的历史里,梁启超、宋教仁、蔡锷、杨昌济以及毛泽东和蒋介石虽然各自成一类,却都曾推重曾国藩。即使像章太炎那样以反满为理路痛詈过曾国藩的人,当其一时逸出反满的理路,也会情不自禁地推重曾国藩,比为“天下之雄”。在这些前后之间各不相谋的评断里,后人可以读出一种历史的公平。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甲午战争之后王文韶接任直隶总督,看到李鸿章留下了一大笔淮军饷需里节撙出来的银子而大叹服。这种东西原本不在官帑的账目之内,前任留给后任是可以带了走而没有带着走。因此久在官场而惯见公私轇轕的王文韶称为不可及。这个情节说明,李鸿章也有能够使人感动的地方。但他始终缺乏一种企求人格圆满的自觉和警醒。出身于淮军世家的刘体智说他喜欢“时时以不肖之心待人”来驭下,而不肖之心笼罩的地方总是没有敬意的地方。在三十多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李鸿章为中国社会做了许多不能不做的事,并因之而常在艰难辛苦而没有逸乐之中。然而不能不做的事在当日中国又是不大容易做得好的事。不大容易做得好的事与没有企求人格圆满的自觉连在一起,便使他常常要身背骂名。其晚年曾自叙,说的是:“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而身当中日一战,遂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之后是“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他半生里戎马、封疆、洋务都是以事功见长才而意不在“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因此事功一旦颠蹶则“扫地无余”。在事功颠蹶的地方空荡荡地见不到一种可以凭吊的人格。
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成为士大夫中自觉地身当其冲者。曾国藩以“挺经”为心传,李鸿章以“挺经”为师承,旨义皆在于倔强自立。因此他们都是能够以世运和国运为抱负的人。但时逢中西交冲,他们又面对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并因之而身在中国社会的剧变和巨变之中久苦于心长力绌。发源于欧西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磅礴东来,一路摧折,中国人在三千年岁月中形成的另一种历史过程便不得不在断肱折胫里奄奄无气。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人的三千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历史过程的人。而后是回应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不能不同时成为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他们年复一年地汲汲皇皇于经世济时,并在汲汲皇皇里心力交瘁形神俱疲。但他们的期望又大半都在汲汲皇皇之中一个一个地落空。曾国藩死于天津教案后二年,他所看到的中国是中兴尚不可见而千古未有之变局已经逼来,暮年四顾天下,常自谓“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唯祈速死为愈耳”。李鸿章死于庚子国变后一年,他所看到的中国已是在由变局而入危局,其临终之际遂死不瞑目。在场的周馥说:“比至,相国已著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我抚之,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余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须臾绝。”
他们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收入本书的文章原本打算编在另一本书里。但舒炜先生和孙晓林女士认为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中心单独成书更集中而醒目。他们对读者的了解和熟悉肯定比我深入,并且他们作编辑的敬业和对学术的敬意都使我印象非常深刻。因此我深信之而乐从之。
来源:微信公众号“上海学”“三联书店三联书情”